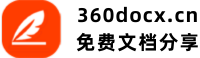【党史学习】遵义会议历史资料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此时,经过半年多准备的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1934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不主张红军与敌军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坚持“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法,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同敌人“决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讲:“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持续18天,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这次战役的惨败,宣告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央将这一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7月,国民党调集3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00余人,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党政军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00余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红军参加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总人数8.6万余人。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出发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这一天,参加长征的每个人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留下的高级干部是: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这些人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后来,他们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的行进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在其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军委纵队的后面担任后卫。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线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粤军这样做,是想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8万多红军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他在广东数年经营的成果必然毁于一旦。此前,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粤军的代表谈判,达成五项停战协议,最重要的就是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粤军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从安远、信丰间通过。10月25日前后,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
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占领了城口镇。红军前锋部队以每天百余里的速度开辟通路,11月8日,红军通过了汝城以南地域。在粤军和湘军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是湘南良田、宜章间的湘军防线。
由于中央红军通过两道封锁线很快,致使何键部因时间仓促,分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线上各要点的兵力,来不及向湘粤边境靠拢。11月15日左右,红军全部通过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是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这是蒋介石真正清醒过来之后,精心布置的一道防线。11月12日,在红军向第三道防线挺进之际,蒋介石发布命令: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追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队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于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湘江防线,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渡口,在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到界首之间。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界首还有80公里。因没有轻车简从,80公里的路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种缓慢行军,让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一条走廊式通道等待了3天。中国革命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
11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此时,湘军进攻兵力超过红军阻击兵力的10倍以上。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顶住,确保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畅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中讲:“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11月30日上午,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12月1日,中央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阻击战到了白热化状态,决定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离全州16公里处的脚山铺一带构筑了第一道阻击阵地,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湘军一轮又一轮地冲击,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反击,厮杀声整整一个白天没有间断。聂荣臻政委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在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的新圩构筑阻击阵地,这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战斗异常惨烈,师参谋长牺牲了,师长李天佑拿起驳壳枪冲出指挥所,政委钟赤兵在15团团长、政委都负伤的情况下,冲出指挥所向15团的阵地冲过去。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构筑阻击阵地,这里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江地点只有几里地,这里被烧成一片火海。位于最前沿的10团团长牺牲后,军团长彭德怀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被在第四师前沿指挥的师政委黄克诚拦住。
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这个军团的阻击战打得特别惨烈,这支从中央苏区出发时1万多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战斗人员仅剩下1600人。
红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红五军团第34师一直担负中央红军的后卫任务,在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他躺在担架上,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壮烈牺牲。
到1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央派出了两支队伍。周恩来称他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闽浙赣苏区,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壮烈牺牲。12月20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围。1935年1月16日,粟裕、刘英等率领800多名官兵突出重围,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红六军团各部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之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萧克续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两个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与他们会合,但这条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通。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红军也进行了军事转移。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后,1933年1月到达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9月,20万川军“围剿”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奋起反击,至1934年2月,双方在战场上形成僵局。1934年6月,20万川军向万源发动进攻,这是关系川陕根据地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5个军参加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8月份,红四方面军发动总反攻,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战术,使川军全线崩溃。1934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红四方面军在枪林弹雨中生存下来,下一步将迎接更严峻的战斗。
1934年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25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开始西征。他们一路拼杀,转移伏牛山,奔袭紫荆关,北出终南山,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共同为后来的中央红军开辟了一块落脚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开展活动。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这时,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企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革命即将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主要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0—1974年),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
会议内容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会议的历史地位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会议的精神内涵
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确定中央领导核心等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路线,独立自主地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变换长征方向,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克敌制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独立自主地领导解放战争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
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落脚点”的确定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夺取长征胜利同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有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核心问题极为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凝聚力,核心就是组织力,核心就是战斗力,核心就是影响力。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奠定稳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提供了有力保障。
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都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应有之义。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全党全军不恐慌不懈怠不放弃,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决定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遵义会议既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对重大危机,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典范。